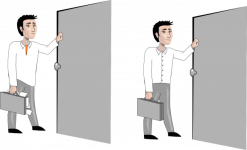鸡司令
1976年防震抗震,我们从逸圃的家里搬出来,搬到了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我们在防震棚里住了一年半。
妈妈买了只母鸡,本来是要杀了熬汤喝的。妈妈还说这鸡有点不尴不尬:不老,兴许熬出来的汤并不鲜;可又不是公鸡,可以炒毛豆吃。这只鸡像是听懂了,很害羞地躲在桌肚子里。后来,我看见桌肚下多出一个鸡蛋。我对妈妈说:“妈妈,一个蛋!”妈妈不信。果真看到那棕红色的鸡蛋,吓了一跳,赶紧去抓一把米給鸡。第二天,鸡又生了一个蛋。妈妈说:“这么杀它,真下不了手,不如我们也养养看吧,既然邻居们都养,这里也有地方。”
又有一天,妈妈抱回一个纸板箱,对我说:“快来看呀!”二十只黄茸茸的小鸡,叽叽喳喳,张嘴朝上,还有两个性急的直接就想往纸箱外跳。
它们很快就长大了,它们长得可比我快多了。我还没摸够黄毛绒的小身子,那身毛陡然就褪了。那时,刚上小学的我开始成了业余的鸡司令。
我说我是鸡司令,小鸡们其实不听我的,它们自顾自地跑。它们的身上也没标图案和符号。我认识它们凭它们的长相和体态。小鸡有各自的脾性,有的温驯合群,总是一步三回头,等别的鸡结伴而行;有的没主张,只管亦步亦趋;有一只却是脸红脖子粗,昂头竖脑,喜欢自己走自己的。它个头长,视线也该高些吧。母鸡不是它们的妈妈,看上去像妈妈,至少也是个阿姨,在鸡群里稳稳地踱步。只是在我给它们撒米的时候,鸡才都跟着我转。
回到逸圃家中的第一个晚上,母鸡和小鸡被妈妈关进了后院。第二天早上,我刚把后院的门打开,小鸡们就叫叫嚷嚷,急急忙忙,赶着碎步子,一起挤进门,一起抬头看了看,就敲打着木头地板,前赴后继地穿屋而过,到了前门口,领头的几只停留了一秒,奋然跳下一尺高的门槛,跳到前院的天井里去了。后头的一拨一拨地跟着跳。最后一个笃悠悠出来的是那只母鸡。
特别奇怪的是,它们没有在屋子里左顾右盼,全都知道往前冲,往前头院子的方向冲。小鸡们对天井还挺好奇,母鸡却总有些若有所思,总想往哪里多迈两步似的。我一直担心鸡要踱出天井,踱出我们家的这进院子。
有一天,母鸡突然就不见了。等我和妈妈没见母鸡在眼前晃动,心头恍惚,异口同声地说:“咦,母鸡呢?”它早已经不见了。抬眼一看,天井东面的门果然虚掩着,母鸡是出门去了。
天色说暗就暗了。妈妈拿着手电筒,走到火巷南面的后园子里,挨家挨户问:“看到一只母鸡了吗?黄褐色的羽毛,不胖不瘦。”
陈家太太说:“哦,黄色的草鸡,原来是你家的呀,我是看见过这么一只鸡占了我家的鸡窝,我踢了它一脚,把它踢走了。”
“踢走了,你怎么踢我家的鸡?”
“我哪里晓得是你家的?”
“哪家的,你也不能乱踢呀!”
“鸡还有不能踢的?”
“你把它踢哪里了?”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一踢,它就跳出去了。”
妈妈不再跟她啰唆,却加快了脚步,这时爸爸也跟了过来。
正对着陈家的门,是后花园的一个木头旋转楼梯。在那平时我们小孩子捉迷藏的楼梯肚子里,躺着我家那只母鸡。手电筒的光照射着它时,它也没有抖动一下羽翅,它好像特别、特别累。把它抱起来,居然身子底下,温热的地方,手电筒还照出了一个带血的软壳蛋。
“它流着血呢!”我叫道。我们三个心事重重地回屋。不过,母鸡,它总还在,总还是找到了!心头又有些宽慰起来。哪里知道,只半个时辰,母鸡,它竟然死了!
夜间我难以入眠,听到妈妈对爸爸说:“好好的,怎么就这样了?哪里想到门没关严,哪里想到它跑出去,偏偏被人踢上一脚。你想想,肯定不止一脚,怎么都踢到流血的地步!往死里踢,你看看,她倒还好意思说,是她踢的。”
“还是别想了,都已经这样了。睡吧,睡吧。”
“它一定是急着找窝下蛋,才占了她们家的鸡窝的。到临了,还下了一只蛋。”妈妈顿了顿又说。
妈妈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都没搭理陈家太太,我自然也没有。我在那个夜里流过泪,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想起来,也会哭上一会儿。我告诉自己,我们家的母鸡再也没有了,我是再也见不着它了。它是丢失了以后,好歹被我们找到的,但它竟还是不见了。
母鸡没了,小鸡们浑然不觉,至少它们没表现出任何疑问和诧异。每天依然是从后院挤到后门,叽叽喳喳地敲击着木头地板,奔到前门,跳下半尺高的木头门槛,到前院的天井。
一天,来了个业余兽医刘先生,看见我的那群小鸡,说,市面上不久要流行瘟病。刘医生说,他可以来给这些小鸡打预防针。刘先生就真的又来了一次,带着针筒和药水。
从此我很笃定地听同学说谁家谁家得鸡瘟了,但并不担心我们家的小鸡。
有天黄昏,看见天井里有两只鸡打蔫、翻白眼,妈妈慌忙叫道:“不好!这大概就是瘟了!”
于是,今天两只,明天两只,陆陆续续地,鸡都病了。
后来我一直问自己,那刘医生的针不打是否就没事?假如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或者即使认识,他也不晓得有鸡瘟这回事,是否,就没有了后头那些事?
当我有些许懊悔的心意,我就容易一直退回去想那些过去的路程,它们的足迹。让它们走回头去,走回后花园,走回搭防震棚的操场,走回纸板箱,走回绒毛的黄色躯体,也许走回到一个孵不出小鸡的蛋。它们并不是按这样的方向走,却是走到了我的面前,走了这么久。那只本来买了预备烧汤的小母鸡,也不是烧了汤。我不知道,这都是谁的旨意,我不知道是谁安排我在这样的几十年后的冬夜,要想起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