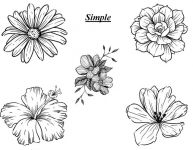关于时间为众生守夜的散文随笔
作家的故乡有两个,一个在纸上,一个在心上。

30岁那年,我将心上的故乡搬到了纸上,用而立之年的清涩与愤慨,真实地纪录了我出生的那个村子——栗门张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用一种远离故乡的姿态抒写着俯视的矫情,以童真的眼光审视着每一个从我眼前走过的人生,从纸上得来的标准来判定是非,处子激情般地抛洒着三十年的沉淀,历史的,传说的,演绎的,真实的,戏剧的,荒诞的,歌着,哭着,敬着,骂着,走着,梦着……披精沥胆地写了四五年,洋洋洒洒地数万言,并渴望用一种史诗般的歌调来诠释群体的生存状态与个体命运,让生命变成历史,让悲剧变成警示,让生活变成文字,让善良变成希望,让行动变成思考,让厚道变成崇高……刀耕火种般地书写着自己的爱与憎,悲与喜,思与忧,折射当下农村在城镇化变局中的歌与哭,梦与醒,苦与乐。
《故乡在纸上》出版后,我自以为在我们村子做了一件天大的事,就像故乡的孩子们说的那样,我们村的作家让栗门张躺在纸上,让过去变成现在,让现实值得怀念,让普通人走进了全国人的视野……事实上,作品的出版并没有我想像中的那样火热,更没有家乡的孩子想像的那么神圣。先是这本书在每年数万个图书品种中并没有脱颖而出,没有引起什么文坛轰动,而后是父亲胃癌晚期,我第一次经历亲痛生死,感受生命的脆弱无奈。连续一年来,我又一次次地奔赴在省城与故乡之间,重温自己心中的故乡与纸上的故乡在创作中的差异,重读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群体的行为方式与做事逻辑,重新思考自己写作的意义及与故乡的关系。
远离十年,再一次走近,蓦然发现我写在纸上的故乡与现实的故乡,还是有着不一样的气质。我也发现在远方根本无法真正地了解故乡——栗门张作为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村的缩影,在农村城镇化的变局中,潜移默化的互联网与电视媒体强力干扰下,已经产生了“润物细无声”的变化,并以一种蚕食的`方式让主导农村几千年的伦理观念在极端事件中呈现出雪崩式的瓦解,让坚守了数百年的道德舆论显得前所未有的苍白无力。尤其是随着生活空间的扩展,人们在农村土地与城市建筑群来回奔波之后,生存空间转换导致身份转化,给每一个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思想异化,曾经的朴实厚道在商业社会与现实利益的讨价还价中,真实的摸得着的金钱关系的你来我往中,让感性的农民越来越急功近利,让浓浓的乡情在相互攀比中越来越无足轻重,让利他法则下积累出的伦理观念分崩离析……曾经唾弃的自私与张扬渐渐地被人们容忍,群体维护的生存法则在机器劳作中越来越老死不相往来,工业复制与强力崇拜的浮躁风气迅速传染……人们除了明显物质条件改善,消费能力的提高与所谓的信息时代下视野的扩展,并没有表现出精神层面的提升与人文素质的明显改善,更没有表现出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和谐与文化积累。
栗门张这几年的变化,超过二三百年变化的总和。变化得,连我儿时一起玩大的伙伴,因为生活环境的变化与距离的疏离,再次对话已是心照不宣的客套与隔膜。从远由近,从他人到自身,尤其是我父亲在病魔的折磨下,他那种对自己以前个人英雄主义的巅覆和自然法则的否定,对生命的无限留恋与对命运的无限愤慨,让我在审视父亲的同时,再一次地审视自己的灵魂,审视身边的一个个过去的,现在的,亲密的,陌生的生命……阅读别人的生命时,再一次阅读自己的作品,思考生活本身时,再一次的思考生活的意义,顿然发现,歌德老先生的高明之处:“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罢了。”恍惚感觉,生活中没有对错,只有对错中的不同立场。现实中没有真正的英雄,只有对英雄的传诵。世界永远没有真实,只有对真实的无限接近……
父亲溘然离世的那一天,我猛然觉得不仅父亲不在了,还带走了我生命中的一道屏障。我体现到了什么是切肤之痛,感知到了什么是生死离别,觉察到无处不在的命运之手,在一个又一个失眠的深夜,我离死亡也是那么的近,好像近在咫尺,伸手就能触摸到悲怆离去的父亲。这时,我发现生命的过眼烟云与生命个体的不可替代性,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竭力要差异化地活在茫茫人海中,每一个人又都是这么孤苦伶仃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人都是那么渴望得到理解,却永远在为知音孤独,但又永远无法真正地彻底理解与相互沟通。在漫无边际的思考与无数生命的不同解读后,我以宗教般的虔诚与赤子般的热忱继续书写着故乡,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重新解构村庄,我才清晰的意识到——听着传说,我们正走进传说。书写历史,我们将要变成历史。纪录真实,心灵却被现实击碎。理性上,我知道故乡,具有三百多年的栗门张就是这样生死轮回着一代又一代地繁衍过来的,可感性上的恐惧,并非用文字就能全部表达,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增加的不仅是年纪,还有时光的年轮,消失的不仅是岁月,还有渐走渐远的青春。等待的不仅是辉煌,还有不可避免的人生谢幕。正如,我在努力而又思辨般地写这个村子,总有那么一天我也会躺在纸上一样。
《抵达生命的彼岸》、《失落的精神家园》、《在记忆中奔跑》,当我忧伤地写出一篇篇回忆我父亲的文章时,我却在忧伤中越陷越深,直到难以自拔地抑郁成病。于是,我又一次次悄然潜回到我们的村子,寻找生死离别中的希望,寻找悲欢离合中的人文精神,以及正在延续的起起落落的人生故事,便写出了《传说中的寨墙》、《沧桑的缅怀》这些以前未曾发现的人文价值与道德传统。用一种发掘的心态,我再次梳理般地探究栗门张时,我感觉事实就像一头大象,每一个人摸到的都不是全部,而是大象的一部分。因此,我不但要继续写作,更应该有修正自己作品的勇气。于是,我又续写了《纸上的痛苦》,用一种秋风掠过天空的心态真实地写下《民间智慧》、《偷鸡蚀把米》这样典型的作品,并根据自己的困惑,写下了《瓦解》、《盖棺定论》、《马失前蹄》这般无限惋惜的伦理之殇。这期间,作为一个而立之后的男人,在对生命意义浴火重生的思考,经历荣誉与泪光的洗礼,我知道,我对村子的写作虽然永远没有真正的真实,却是对真实的无限接近,对尝试创作经典的心境磨励和一丝不苟的艺术抱负。
“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很早,我就读过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的这种观点,并竭力维护他的观点警示自己的创作。每一次回到村子,看着物是人非的改变,看着越来越城镇化的楼房及一个个曾经熟悉的父老乡亲的消失,看着新陈代谢的一张张陌生的新面孔,想着故乡在时间面前一天天地老去,我已经没有了作家的感觉,也没有三十岁前是非评判的能力,更没有所谓的责任感的矫情。我有的,只有对村子的纪录,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意义的原点回顾,以及我发现自己的灵魂在世俗漂荡的悲苦与独立秋风中的怆然无助。
时间的线性,决定了每一分一秒的独一无二性,也决定了每一个差异化人生的独一无二性,更决定了我对故乡每一次纪录的独一无二性,并因我寻找精神归属感的固执与执迷,有了《故乡在纸上》每隔几年的新版本和栗门张的独一无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