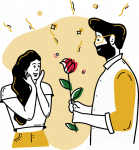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
「1」
我一直记得自己九岁时阿公的模样。那时的他有结实的身板和一双异常粗糙的大手,那双大手总用来织补渔网;常年风吹日晒的黝黑肌肤上,散发出一种海的气味;笑起来额上有深深的皱纹,像车轮碾过的潮湿土地。
这一年,我的父母在经历无数次的争吵打闹后,终于分道扬镳,把年幼的毫无准备的我丢回老家,让阿公和阿婆照顾。元宵节的鞭炮声还未止息,我就来到沿海的乡下村庄。我甚至没有多带行李,只背了一个红色的双肩背包,包上挂着两年前他们给我买的粉色兔子玩偶,包里只有一套换洗的衣服。
车子在热带沿海老家古旧的屋门前停下,那棵在风中摇晃的龙眼树下,灰壳子椿象随着龙眼树花飞舞,然后挣扎着跌落在尘土里,空气中弥漫着椿象令人窒息的臭味。
两扇木门的后面,阿公在院子里织补渔网,阿婆一手拎着母亲为我准备的行李,另一只手来拉我。我没有回应她,只是倔强地站在龙眼树下。或许是热带阳光的原因,或许是憋了一路的眼泪,使得自己浑身湿淋淋的。车子驶离后,我号啕大哭。
哭声持续到夜晚,白炽灯的灯光微暗,飞蛾成群扑来。阿婆第三次把饭端给我时,依旧不得回应。阿公站在门外,摇着头劝她作罢。我躺在阿婆咯吱作响的木床上,罩在泛黄的蚊帐里,只觉得天塌地陷般的无助与悲伤。我终于确定,自己无可挽回地被丢下了。明白以渺小的力量倾力呐喊,也不会被远方的父母听到,我索性闭上嘴巴,不吃饭,不说话,企图以孱弱的别扭沉默地反抗。
第二天,阿公早早就出门了,直到傍晚才回来,手里抱着一个黑糊糊的大蜂巢。他拿来一个篮子,把蜂巢里蜜蜂的幼虫抖落。它们大部分是乳白色的似缩小版的蚕蛹,少部分是浅黄色及浅褐色的,长着柔软的羽翅和透明的六足,落在篮子里,散发出一股松香和蜂蜜甜。
阿公挥刀破开一个椰子,将又厚又硬的椰子肉刨成细丝,拿五花肉切成丁,下锅炒炸出油之后,再放入蜜蜂的幼虫与椰丝。铁铲翻炒的间隙,一股无敌的诱人香味穿墙透壁,铺天盖地而来,从鼻腔一直窜入心肺,让人忍不住猛吞口水。不用哄也不用喊,我已跑过去黏在锅边,小狗般贪婪地嗅着。此时,我的世界已经被一种味道霸道而温柔地侵占了。
蜜蜂幼虫被炒得外皮酥且多汁,混着椰奶的香味,我嚼得像放烟花一样噼里啪啦,耳朵里仿佛冒出了叮咚之泉,使人舞荡起来。阿公看着我,眯起眼呵呵笑:“这就对了,吃好吃的,吃香香的,不高兴的都丢掉。”
我从未吃得那么饱,也从未睡得那么好过。
「2」
或许孩子容易对新环境产生抗拒,但同时也保持了新鲜感和好奇心,以至于一旦融入新环境,总是全身心地投入。但一年中,我总有几天仍旧很强烈地想要回到父母身边,会在电话里对他们装乖,挂了电话却对阿公阿婆哭闹。只是次数渐渐少了,在更多的时间里,我开始融入当地的生活,放学后和朋友们到海边捉螃蟹,夜里拎着一盏灯去田里捕萤火虫,回到家陪阿公看电视,临睡前缠着他给我唱曲子。
一年后,母亲终于来接我了。临走前,我想等阿公回来,跟他好好道别,可是母亲等不了,飞机也等不了。就像那年匆匆把我丢下一样,她又匆匆地把我带走了。我抱着阿婆为我准备的各种鱼干,闻着袋子里鱼干散发的气味,一走就是三年。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无数次想象,阿公回来后发现我离开了会怎样。他会不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一边织补渔网,一边不时地抬头听屋子里还有没有我的动静?会不会新编了一首曲子却不知道第一时间要找谁分享他的乐趣?会不会傍晚站在那棵龙眼树下,穿着背后泛霉点的旧背心,摇着芭蕉扇子等着我放学归家?
一切都因为我没能与他好好道别。
我给阿公打电话,他说长途电话费贵,不要常打。我确实打的次数越来越少,通话时间也越来越短,有时我握着话筒,除了反复问他吃得好不好,身体好不好,已经不知道要再说什么了。
两年后,看起来一直很健康的阿公被检查出骨癌。暑假时,我迫不及待地回去看他。门前的龙眼树结了沉甸甸的果子,被阳光晒裂的果肉吸引了许多蜜蜂在其中穿梭。
「3」
老屋年久失修,散发着一种陈旧的气味。阿婆的头发比过去更白,脊背比过去更弯。阿公已不能走路。我走进屋里时,看到他平躺在床上,嘴里不停地发出被病痛折磨的呻吟,比身边的老风扇发出的声音更令人悲伤。他招呼我过去,问我有没有吃饭。我扭过头,不让他看见我脸上的泪水。
“要吃好吃的,阿公不能给你摘蜜蜂了。”他克制着不发出疼痛的声音。
我偷偷地擦掉眼泪,把脸凑到他面前,闻着他身上渐渐消失的海的气味。这气味曾让年幼的我那么喜欢,那么安心,可是以后我再也闻不到了。
午后的阳光灼得粗糙的水泥地板烫人,我极其缓慢地走出空气黏稠的院子,呼吸困难,想起阿公看我的眼神,像那远远相隔的龟裂的池塘。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吃了很多龙眼,甜得喉咙发烫,心里却又苦又冷。眼泪一颗一颗滴下来,鼻腔里仿佛又弥漫着一股椿象的臭味,我好像回到被父母丢下的那一天,倔强地站在龙眼树下。
又想起阿公为我做的那道绝美鲜香的无名菜,至今我都不能很好地形容它,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但它在我的记忆中达到了一个与情感交融的制高点,在我最哀愁的童年时光里,如一抹蜜糖,覆盖了苦涩和酸楚。在煎熬着我幼小心灵的池底时光中,它猛地把我拉出水面,让我重新燃起对一切未知的美好期盼,更使得一个孩子和一个老人的心灵相依相靠,使得长夏永不凋谢。
被骨癌折磨了两年的阿公,在临终之际,用瘦骨嶙峋的手拉着我,艰难地说:“要吃好吃的,要快快乐乐的。”
我握着他的手点点头,说:“我会记得你的话的,阿公,我已经体会过痛苦,也懂得了如何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