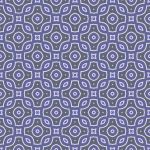一只菜虫
雨天,我在牛津的家里安心写作了几天。
“自己去花园里摘菜吃。”我妈出门时留下话。我照办了,走到空气冷冽的户外,从湿润的黑土中拔了萝卜和青蒜,又摘了点菠菜叶子,洗了之后切好,放进蒸锅里。午饭时间,我就坐在饭桌前,面对着一盘子蒸菜。我撒了点盐,又滴了些橄榄油。接着我发现,被蒸得懒洋洋、蔫不拉几的叶子之间,有只漂亮的小菜虫,有两三厘米长,淡绿色,很可爱地躺在那儿,颜色清新、通体干净、冒着热气,像婴儿奶嘴那么鼓鼓囊囊的。
我刚想把这只虫直接扔出门去,突然停下了。因为我突然想起几个星期前写过一篇长文,描述我在中国吃昆虫的经历。那是我研究的一部分,到四川一家专门做昆虫菜的餐厅吃饭,吃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特色菜,其中有蜂蛹、柴虫和爬沙虫。
我在台湾犯了个错误,铁了心要和一位著名美食作家争个高下。“嗯,虫子嘛,吃过啦,”我吹嘘着自己在四川吃过的很多虫子,有成虫,还有蠕动的幼虫,楚先生咧嘴笑了。“嗯,”他深吸了一口气说,“我在云南的一家餐厅,服务员给我拿来一只活的菜虫,有好几寸长。叫我一手用大拇指把它的头按在桌上,另一只手把身子扯下来,就那么直接吃掉,非常美味哦。”此话一出,我很快闭了嘴。
有时候我的西方朋友们会发现我像个中国人那样行为做事,比如吃着橡胶一样的东西,边嚼边含混不清地赞叹,或者喝汤的时候发出奇怪的声响。一般来说我都会努力让他们安心,戴上纯粹英国人的面具,自嘲什么都吃,或者觉得东西好吃时隐忍着不发出声音、不开口赞叹。但偶尔我也会忘,那副面具就滑下来,一块骨头就那么粗野地扔在桌上,可怕的声音就那样震撼着同伴们的耳膜。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这声音竟然来自一个(他们所认为的)正常的英国女性。
再回到牛津我爸妈家,深深地凝视着那只菜虫。我心想,这要是在中国的某个昆虫餐馆,我肯定二话不说就把它吃了,为啥在这里却犹豫不决呢?不过,我也想到,吃我爸妈花园里的菜虫就真的太越界了。根本没有借口,不像在中国可以用“入乡随俗”搪塞过去。要是我吃了这只刚刚蒸熟,躺在我妈有垂柳图案装饰的盘子上的英国菜虫,我那些英国朋友就会更为震惊,他们会难以置信地望着我,这个人是不是疯了?我上下打量着盘子里那个绿色的小东西,不得不对自己承认,就算再怎么努力,我也不会觉得吃掉它是个多么惊世骇俗的想法。就算我能勉强挤出一丝害怕的表情,那也是非常虚伪的,只不过是想安抚假想中那群同胞观众的情绪,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厌恶。我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已经不再只是个具有冒险精神的英国旅人,在异国他乡为了拉拢和讨好本地人而去硬着头皮吃一些我不愿吃的东西。旅居中国这么多年,我和我的口味已经有了深刻的改变。英国的朋友们也许觉得我看上去没什么两样,觉得我仍是他们中的一员。实际上,我已经跨界,去了“另一边”。要不要吃这只菜虫,问题绝不在于我敢不敢吃,而是在于我敢不敢这么旗帜鲜明地表示,老娘一点儿也不管别人怎么想。
你应该猜得出后事如何。列位看官,我吃了那只菜虫。我承认,我咬了那柔嫩的身躯,我用舌头感受到那小小的奶嘴一样的东西,然后吞了下去。什么也没发生。没有天打雷劈,没有地动山摇,没有愤怒的英国神灵因此降下暴雨洪水。菜虫本身味道寡淡,吃着水汪汪的。我感觉也还好。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我又咬了一口,把头也给吃了。接着我平静地继续午饭,挺好吃的。
但那頓午饭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仿佛是一道门槛,一个自我认知的灵光时刻。那之后的几周,我不管到哪儿,心里都觉得,我终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