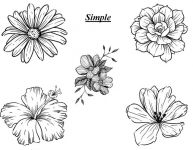茅草岗是我人生的胎盘散文随笔
在江北圩区,村庄与村庄没有明显的区别,都无一例外地撒落在画满沟渠水网的平整田畴之间。有村庄的地方虽然都有树,但没有名贵的树,大多是那种普通的苦楝、乌桕、泡桐、梧桐以及桦树和梓树。农户家的房子无论是草屋还是瓦屋,都建得非常简易,墙以土坯,或土坯、青砖混砌为主,全用青砖的不多,顶上盖的要么是茅草,要么是灰色的大瓦片,盖黑色小瓦的凤毛麟角。

村庄有大有小,大的几十户人家,小的只有几户人家,无论大小村庄,均难见年代久远的古屋。因为紧靠长江,常遭水患,遭遇一次大的水患,房子就要经历一次劫难,或被洪水冲垮,或因水浸而倒塌,能够历水患而幸存的房子少之又少。
生活在圩区村庄的人总是有着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他们被长江哺育,又害怕长江,不知道哪一天长江会发怒,会毫不留情地卷走他们辛辛苦苦置办下的微薄家业。过着面朝黄土面朝天的日子,他们辛苦劳作的剩余价值不多,即使是置办下微薄的家业也极其不易,因此除了勤劳之外,他们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这种节俭,局外人很难想象。
4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我便出生在这样的村庄里。我所在的村庄叫茅草岗,其实,那里只有茅草没有岗,算得上岗的无非就是村庄里家家户户垒得高高的屋基,因为怕水淹,他们不得不将屋基尽量垒高,其实,垒得再高也只是一种自我安慰,长江的圩堤一破,屋基垒得再高也无济于事。
这个叫茅草岗的村庄大约有30来户人家,沿长江圩堤排成没有规律的曲线。圩堤外面是依次是一条100米到50米宽窄不等的杨树林带,林带外面是荒滩地,荒滩地的外面就是江滩了。每年长江的枯水季节,荒滩地可以种一季作物,但总是种得多收得少。这一季的作物大多成熟在汛期前后,汛期来得迟几天,还有收成,若来得早几天,就会颗粒无收,已经成熟八九分的作物眼看着被江水吞噬,总是叫人心痛得直掉泪。
因为是棉区,圩堤里95%以上的耕地种的都是棉花。圩堤外的荒滩地则大多种的是水稻,获得的收成是村里人口粮的贴补,没有了收成,便只好全靠回销粮度日。吃过回销粮的人或许都有很深的记忆,一是回销粮不一定都是大米,有时候是老玉米或干地瓜片,即使是大米也是现在根本无人问津的陈化米;二是定量一般都不够吃,只好以瓜菜代。
伴随我整个童年的就是这个叫茅草岗的村庄。从记事起,恐惧和饥饿就一直如影随形地纠缠着我。村民口口相传的关于长江破圩的故事,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一到长江汛期,我无时无刻不担心圩堤溃破,每个夜晚都会被洪水滔天的梦境惊醒。在漫漫黑夜里,我内心的忧患意识被恐惧的梦境催生,并一点点长大。
有两种东西是我儿时的最爱,一是长江圩堤外面杨树林里的茅草根,是邻村桑园里的桑葚。因为回销粮不够吃,江外荒滩地偶尔的`收成又被节俭的父母换成了砖瓦,人口本来就多的我们家总是过着吃不饱的日子,童年的我因此饱受饥饿的滋味。于是,杨树林里的茅草地就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茅草根一节一节的,就像缩微了的甘蔗。将拔出的茅草根放在嘴里嚼,有淡淡的香甜味,我经常是嚼着嚼着,就暂时忘记了饥饿。
桑树结桑葚时不啻我的节日,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每天泡在邻村的桑园里,在我眼里,青的、红的、紫的桑葚,是人世间最美的美食。尽管因此胃里有了充塞物,但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有时候,因为误食了毛虫爬过的桑葚,结果嘴巴种得比馒头还要大,那种火烧火燎的滋味,不是亲身经历着不能体味。
茅草岗,这座最初哺育我生命的村庄,不仅决定了我童年的生活,而且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