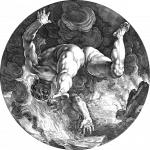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散文随笔
一、村庄,装满了少时的趣事

秋收时节,田野里总是蛙声一片。
村庄前面有一片梯田,稻谷收割后,就剩下光秃秃的稻茬,齐刷刷站在稻田里,远远望去,层次分明的梯田就像铺上一大块浅黄色的被单。
一阵小雨飘过,梯田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蛙声,和着田边大树上高声啼叫的知了,就是一曲抑扬顿挫的田园交响。远方的两山之间,一条硕大的彩虹得意洋洋,呈半圆形横跨。
稻田里的水浅得刚好漫过我和小妹的脚裸。
我们浑身沾满泥巴,半低着身子,在稻茬之间捉小鱼。田里那些野生的水白菜水芹菜依附着稻茬生长,开出嫩黄色的小花。小花下,那些平时游泳很厉害的小鱼在稻茬间奔走,在疲惫中任我们戏弄。
“哥哥,我们把这些小鱼捉了,要是到了天黑它们还不回家,它们爹娘找不到怎么办?”七岁的小妹浑身脏兮兮的,手里拿着一条拼命挣扎着小鱼,看着鱼儿哀求而可怜的样子,就问我。
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是呀,鱼应该是有爹娘有家的,就像我们小孩子,平时我们小兄妹到了晚上不回家,父母总是到处找,特别是母亲,扯破嗓子村前村后满田满地满山满坡地叫着我们的乳名,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
那时候家里特别困难,捉到小鱼是没有油煎炒的,没有油鱼就会沾在锅上,我们一般是在田边捡些稻草杂木之类的柴火烤着吃。想起了香喷喷的烤鱼香,小鱼不回家它们爹娘着急的问题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沉下脸来对小妹说:“就你那么多问题,你不想吃鱼了吗,要想,就赶紧捉!”
我也很奇怪,这些稻田里的水是从邻近的山箐沟里引来的,稻谷收割后用牛把田犁翻过来,放干水晾干后,就把田里的土坯打成垄,还要种小麦蚕豆豌豆油菜之类的,每年如此,这些小鱼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田里的水干了以后到哪里去,也许是它们躲在某一个小水潭里蛰伏待机也未可知。
那些小鲫鱼成群结队在稻茬里游走,我们小孩子是捉不完的,问题是它们为什么长不大,如果长成大鱼我们就难捉到它们了。
“哥哥,哥哥!我要‘老幺马螂’。”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几只大蜻蜓耀武扬威地排着纵队从我们头顶上飞过,我们地方语言叫这些特大蜻蜓为“老幺马螂”,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也许是民族语言的译音吧。小妹看到大蜻蜓,立马转变了视线,抬头看着大蜻蜓飞到不远处的田埂上停下来歇息,就嚷嚷着对我说。
这大蜻蜓身体碧绿,宽大的翅膀透明,圆圆的大脑袋上圆圆的大眼睛滴溜溜转着。它们不同于傍晚时分漫天乱飞的那种咖啡色的小蜻蜓,也不同于红的黑的蓝的翠绿的那种数量稀少精灵古怪的杂蜻蜓。大蜻蜓数量不多,总在稻谷收割时节出来,大部分是一只,有时候也有三五只在追逐嬉戏。
小妹知道我抓大蜻蜓的能耐,一般是用一支杨柳条或者蒿枝条扎成圆形,再用稻草像蜘蛛编网一样编在圆圈中,然后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扎着圆圈,看到成双成对头尾相连在一起的大蜻蜓飞累了,歇在稻茬或者田埂上的时候,悄悄地盖下去,就捉住了。
只要捉住一对,就把母的放飞了,把公的用一根线拴在翅膀之间的细腰上,再用一根蒿枝条拴着线,只要站在田埂上,不断挥动手里的蒿枝杆,边挥动还边念老辈人流传下来的童谣:“喂,老幺马螂,快过来!你爹在这儿,你娘在这儿,你哥在这儿,你妹在这儿。”公蜻蜓飞舞起来之际,那只放走后重情重义的母蜻蜓就会找亲访戚呼朋唤友,零零散散的大蜻蜓就从其他地方飞来,解救被拴住的公蜻蜓,只要公蜻蜓的同伙来解救时沾在一起,把线拉下来放在田埂上或者稻茬上,就很容易地捉住了。
那只用于引诱同伙的雄蜻蜓,可是功臣,我们好好饲养它,打苍蝇给它吃,它飞累了饿了的时候,也不管自己还被拴着,就用几细细的爪子捧着苍蝇大快朵颐。
抓大蜻蜓一般只有男孩子能做到,因为要抓住一只公的,很多时候,要抬着那根长长的竹竿,胆大心细地跟着黏在一起飞的蜻蜓夫妻追若干丘梯田。小女孩一般是用手抓房前屋后稻草之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小蜻蜓的,她们也是有童谣的,看蜻蜓歇着的时候,从它身后悄悄地走近,嘴里小声唱着“马螂哥哥歇歇,你的'屁股给我捏捏,我的板凳给你坐坐……”那些蜻蜓就乖乖地就真让她们抓住长长的尾巴了。
“我没有带着竹竿,抓不到它们。”我对小妹说。小丫头嘟着嘴,满脸不高兴。
远处的彩虹伴着小雨回家了,只留下山岚水秀,近处依旧蛙声一片,知了啼鸣。
二、村庄,缠满了游子的情丝
经年累月,村庄没有长大,它的儿女在顽皮嬉戏中却长大了。在一个清晨,在淡淡的雾霭中,村庄用期盼而浑浊的双目,深情地送走了他的儿女。
踏着那条山路,像人生一样弯弯曲曲一直通向远方的山路,来不及追忆逝去的童年,告别嬉戏在牛羊之间的懵懂少年,抚摸熟悉的风情,话别野花野草,大山的儿女走出村庄。
从此漂泊流离,成为浪迹“天涯”的游子。
天之涯,浩瀚无垠,游子是一只孤零零随风飘飞的风筝,在时而风雨时而彩虹的空中毫无目的,任意飘荡。不论多高多远,不论贫贱富贵,不论是东南风还是西北方,用情抽成丝的风筝线,一直系在村庄之上,系在慈母心坎。
关山万重,直把他乡做故乡。这一别呀,就三十多年,远去了严父慈母,忘却了青梅竹马,只留下两鬓斑白,只留下村庄的缩影,印刻在记忆中。
求学路漫漫,感知几多愁。
学校旁边,依旧是一片稻田,只不过不是梯田,是一马平川的坝子,是阡陌纵横的画作。相同的是稻子收割后,在田埂上留下了一个个高高的草垛。
中秋时节,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和我一起,拿着学校发给的一个巴掌大的小油饼,沿着窄窄的田埂,爬到草垛之上,用手指一点点搬着油饼吃,看天上月亮在云彩间游走,看数不胜数的星星闪闪烁烁。
“月是故乡圆”,是因为游子的心系在故乡。我们只听蛙声,只看星星和月亮,我们不说话,
一对情侣踏着朦胧的夜色从草垛下的田埂上走来。
“哥,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要保护我呢嘎(呢嘎是方言,好不好之意)。”女的柔声说,声音还带有童音。
“当然!”男的毫不犹豫地回答。“出来读书之前,叔婶就交待我了,要好好领着你。”
“哥,你真好!”
他们倚在草垛一则,紧紧相拥。他们不知道草垛之上,躺着我和下铺的兄弟。
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时,我想起了家乡的小妹,不知道她还好不好。
愁绪伴着情丝,飘渺之中忽东忽西。只有游子,迈不出大山的羁绊。
一山分四季,四季存悲欢。
那些年山里大多没有通公路,偏僻的山区贫穷落后。我和区公所的一个干部一起,深入到山山之间的小村庄,去了解需要供应回销粮农户的情况。
我的村庄在另外一个大山里。揣着青春的激情,揣着对故乡的眷恋,走进一个个村庄。大山里的任何一个村庄,就像我熟悉的村庄,走进一个个简陋的农家,仿佛就是我的家,看到一个个勤劳质朴的父母,感觉就是我的父母。
“哎呀,总算找到你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和同事走到一个村公所所在地,满身汗水未干,村上的一个干部迎上来焦急地对我说,“邮电所的老普摇电话,找了好几个村公所了,就不知道你在哪个村庄。你姐打电话来说,你爹病重了。”
披着夜色,拿着那装三只电池的手电筒,连夜走了三十多公里山路,天亮的时候,我回到区公所。第二天搭着拉山货的大车,赶回家去。
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走了,伴着他心爱的马帮寻着马铃声远去。游子的心碎了,碎在村庄之上。
难说你有情,难说我无情。
小妹在村庄袅袅升腾的炊烟中渐渐长大,山里的灵气熏陶出她俏丽的容颜,十八岁的青春,溢满了少女的爱恋。
那一年她走了,无声无息地走了。那是在一个集镇赶集的日子,跟一个外省来本地做活的男人走了。等我知道的时候,就不知所踪。父母告诉我,她让同去的小伙伴带话回来说,不要找她,她安顿下来,会和家里联系的。
此后多年,再也没有联系。
亲情,爱情,很多时候难于逾越。她是在很小的时候父母从另外一户要好的人家抱养来的,她的亲生爹娘说,她家姊妹太多,儿多母苦,加之天灾人祸,那年她家无意间着了一把火,简陋的房屋付之一炬,本来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说我家姊妹少,于是就送给我娘。
小时候我不知道,她也不知道。
我出去读书后,她和年迈的父母,承担了琐碎的家务,姐姐们先后出嫁后,她悉心照顾着父母。她在等待自小领她顽皮捣蛋的哥哥回来。
望穿秋水,望断天涯,哥哥依旧在远方,在另一座大山深处。多少年的等待,她看到哥哥带回来了一个女朋友,说是她的同学。
万念俱灰,她走了,离开了熟悉她的村庄。
“快叫舅舅!”又若干年后的一天,她带着她的爱人和孩子神奇地回来了,让两个孩子叫我舅舅。她的眼神里,早已褪去了当初的清纯,只留下幽怨和顺着脸颊不断流下的泪水。
我的心碎了,像当初找寻她时候一样。
村庄脚下,我带着她的孩子和她,走在熟悉的梯田之间,走在窄窄的田埂上,走在往事之中。
三、村庄,刻骨铭心的来去
从村庄出发,乘着人生的列车,一个个站台从眼前滑过,起点终点,在循环往复中轮回。
“喏,孩子,那就是我的家。”年前的一天,已经两鬓斑白的我,带着妻子孩子,乘着新买的轿车回到家乡,在村庄前面的山梁上歇息,指着远处那个朦胧的村庄对孩子说。
看到熟悉的村庄,仿佛看到自己的亲人。
大学毕业的女儿不顾旅途的疲劳,下车边采摘着路边嫩黄色的野花,边兴高采烈地说:“爸爸,你老家风景真好,真漂亮!”
妻子说:“是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茅草窝’,这是你爸爸的根是他的魂。”我知道,她总厌烦我,说就知道天天念着要回老家。
当年弯弯曲曲的山路,现有已经通了简易的水泥路。路边,偶尔驶过农用车和摩托车,就驾车的人不知道我,他们太年轻。
鸡鸣狗吠,炊烟袅袅,村庄还是那个村庄。
父亲死后,我调到了小山城。古老的山城,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破旧的瓦楼房,逼仄的街道,古老的商铺,像魔术大师变魔术一样,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只有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伴着红男绿女在霓虹闪烁醉生梦死。
母亲一个人还在老家。
多少次带信回村庄,多少次苦口婆心地回家劝说,让年近八旬的老母亲一同来和我居住,她就不来,说家里还有她的猪她的鸡,还有那间老屋,还有门前那棵桂花树。
用于生活费的钱是按时寄回去给她老人家的,但天高海阔的亲情,不是钱架起,是血脉相连。
母亲对我说:“孩子,外面再好,也不是你的家。你要记住,叶落归根,你的家在大山深处,在这个偏僻的村庄里。当年你爹忙死忙活,带着一家人回来,就是为了回家。”
只要有人来山城,母亲总会带些自己种的蔬菜瓜果之类的来。我想起了当初出去读书的时候,母亲在深夜,用一块小红布缝制了一个荷包,里面装满了茴香籽,让我时刻贴身戴着。
茴香,回乡。
母亲在拽着那根风筝线呢,每夜的梦中,仿佛听到老娘在呼唤我的乳名,在叫我回乡。
记得读小学时候,去大队上的学校要经过一条箐沟。有一天放学,和小伙伴嬉闹不注意就掉沟里了,被冲了很远一段,被人捞起来背回家。
母亲知道后,虽然我好好的,却哭得死去活来,边哭边骂:“你个忤逆中,我家才有你一个儿子,你要是死了,你的魂被沟里的水带去远方,以后我们去指望谁。”
边骂边忙颠颠的去熬老姜加红糖水。
过天,她一手牵着我,一手挎着竹篮子,篮子里装着一个煮熟的鸡蛋放在一碗米上,还有香火纸钱之类的祭品,到我摔进沟里的地方“叫魂”。摆好祭品,烧香磕头,她口中念念有词:“过路的,赶马的,病死摔死的,不要来找我家孩子,要钱烧(捎)给你们……孩子,吓着回来喽,远处喊你来近处,近处喊你你回来。回来喽,回来喽……”
我是不相信那些迷信的,但看到母亲认真虔诚的样子,大气也不敢出。
来时一个命,去时一个病。那年母亲病重了,我手慌脚乱地把她老人接出来,到小山城看病,到市里医治。
“孩子,最近我总是梦见你外婆外公,梦见你舅舅和你爹,估计娘这次是逃不过劫难了,不要再破费钱了,娘是老了,像熟透的果子。”母亲躺在病床上,气喘吁吁地交待我说,“趁我还有一口气,你一定要把我带回老家去,带回那个村庄去。”
回到村庄,母亲趟在铺在堂屋里的简易床上,一会儿抚摸着她孙女稚气的小脸,一会儿抬眼看着简陋的老屋顶,几日水米未进。弥留之际,她对我说:“孩子,你记住,以后一定要回家来。”
我们一家伫立在父母留下来的老屋前。
断墙残壁,蒿草摇曳。老屋已经面临坍塌了,只有门前那棵桂花树,依旧生机盎然。
村子后面,就是大山。
山里有我童年放牧牛羊的身影,还有不尽的回忆。那些憨厚朴实的老牛,那些长胡子短胡子的山羊,早已不知魂归何处。只有春日的风吹开了年年盛开的野花,夏日的雨催生着山里层出不穷的蘑菇。只有小妹的身影,屁颠颠跟在我身后,期盼的看我上树掏鸟给她玩。
只有山腰上的一小片土地上,父亲母亲在静静的休息。
我想起了父亲的话,他说人占三块地,种庄稼的山地、屋子地最后当然是墓地。
我出生在老屋,生长在村庄。每次伫立老屋前,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
“我们去你姑妈家吃饭。”收回思绪,我对孩子说。村里还有一个姐姐,在艰难困苦,恬恬淡淡中生活。历经了多少苦,大山的女儿始终没有走出大山。
每次回来,姐姐一家总是很高兴,翻箱倒柜,倾其所有,都要给兄弟一家做出最好吃的。
姐对我说:“兄弟,你年纪也差不多了,不要忘了娘的话,还是回老家来。找点钱修修老屋,还是能居住的,城里空气不好,对身体也不好,何况只要在村子里,以后逢年过节,爹娘总能闻到香火,吃到你们带给的饭菜。”
当地人总是传承着一种习俗,逢年过节,总是要给死去的人烧纸钱,供奉祭品,特别是最亲的人,说远去的亲人是能感知到的。
村庄,老屋,亲人。
我怎么能忘记,我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