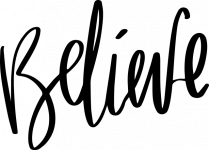那个为我推开一扇门的人走掉了
陶瓷兔子,文艺与理性兼备,傲娇和有趣共存,解局情绪化,专治玻璃心,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天天成长研习社”,已出版《决定你上限的不是能力,而是格局》《所有的成长,都是因为站对了位置》《成熟》等著作。
初二那年,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我离开生活了13年的南方小城,转学到西安。
变化来得太突然,只有一所普通中学愿意接收我。我的班主任是个30多岁的矮个儿女人,她从近视镜上方的空隙中瞅我:“你就是那个从黄冈中学转过来的女娃?”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她笑了一下,用那种“今天天气不错”的随意语气说:“给你个班长,你来试试吧。”
我妈很开心,觉得老师很照顾我,有个班长的身份,我也能更好地融入新集体。回家的路上,我妈还特意拐进超市,挑最贵的糖买了一大包,叮嘱我一定记得分给大家。我被我妈为安抚我而刻意表现出的乐观所感染,也逐渐将对未知的惶恐抛之脑后,开始兴奋地规划起新的生活。
可我们忘了同一件事——树敌莫过于捧杀。当我给大家发糖的时候,一个女孩将我给她的糖拨到一边,半是挑衅半是轻蔑地用方言说了句什么。我初来乍到,陕西的方言一句也听不懂,只好硬着头皮用普通话回问:“你刚才说什么?”
“连话都听不懂,还当班长呢,丢不丢人?”这次她换了普通话大声说出来,跟她关系好的几个人立刻发出起哄的嘲笑。事后,我同桌悄悄告诉我,那个女孩就是之前的班长,干得好好的,老师却连招呼都没打就换了人,这才拿我出气。
开学第一天,我就已经树敌,而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个开端。
我们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上课的时候总习惯使用方言,我因为听不懂,只好在课上低着头看书做题。两个礼拜之后,她把我叫进办公室责问:“上课为什么不听讲?你是对我有意见?”
我小心翼翼地用最婉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听不懂方言的事实,可换回的不过是一句:“我教了这么多年书,别人都听得懂,就你听不懂!别以为自己是好学校转过来的就矫情!”
我沒法儿辩解,只好花更多时间预习、复习,可对一个刚满14岁的小孩来讲,靠自学能理解的内容毕竟有限。我一向引以为傲的数学成绩在期中考试之后开始不受控制地下滑,我学得越来越吃力。
那是一节再普通不过的数学课,班主任在黑板上出题让我和另一个同学上去解答。我至今记得那道题是关于三角形平分线的。那个同学在我身边运笔如飞,我却一点头绪也没有。背后同学们的视线像是个放大镜,而我就是那只被聚焦对准阳光的蚂蚁,只觉灼热,却半分动弹不得。
下一秒,我就被班主任揪着校服拉到了讲台前。她一手拉着我,一手用板擦敲着我的肩膀。
“好学生,这就是黄冈转来的好学生!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你怎么配当班长?”
板擦敲得不重,但每敲一下,都会有五颜六色的粉笔灰扬起来,落在我的头发和校服上。因为我的出现而被剥夺了职位的前班长,在下面附和着班主任大声起哄。我在一片细碎的哂笑声中落下泪来,却只换来变本加厉的嫌弃:“我说错了吗?你还有脸哭!别以为你是名校来的就了不起。反正我讲课你也不听,以后上数学课就给我站到走廊里去。”
我的自尊像是一颗掉在地上的紫葡萄,被她毫不留情地踩出黏腻的汁水。我对学校的厌恶感很快从数学蔓延到其他科目,各科成绩一跌再跌,而我也成为班主任每次班会上都会拿来批评的典型。前班长笼络了一群亲信,整天对我冷嘲热讽,给我起难听的外号,编造各种恶毒的谣言。
被欺负的事我无法跟父母开口,一是怕他们担心,二是怕被反问一句“为什么人家不针对别人,只针对你?”14岁,正是崇拜权威和迷信集体的年纪,觉得老师不会错,也觉得大家不会错。可如果他们都没错,那错的又是谁呢?
我在这里没有朋友,那时又没有手机,跟远在千里之外的好友通信毕竟不便,几乎每天晚上我都是哭着入睡。学校的顶楼都上了锁,我就在放学的时候仔细观察校门口的车流,默默思考着在哪个时机从哪个位置冲进去,就能一了百了。
现在想来有多幼稚,那时候就有多想死。就在我第N次站在路口看着车流的时候,有人在后面喊我,我回头看到体育老师老张。
老张快50岁了,身板像座铁塔,总是不苟言笑,上课从来都是“800米跑——蛙跳——自由活动”的“三板斧”,除了不得不开口的指导,一句话也不多讲。
他叫着我的名字,而我像是有好几百年都没听到过有人叫我的名字了——同学中没人理我,老师们说起我都直接用“黄冈来的”指代。
可我不叫“黄冈来的”啊,我也有名有姓,我的名字很好听,那是父母对我未来的期许。
粗线条的老张大概不明白,他不过是叫了我一声,我为什么就站在马路牙子上哭成了泪人。但他还是什么也没说,看着我一边哭一边跑远了,自己也就回了学校。第二天上数学课,我又像往常那样被罚站在走廊上,老张慢悠悠地踱过来,示意我跟他走。
“李老师会骂我的。”
“你不管,我跟她说。”
数学课常是早上的第一节,操场上还没有班级来上体育课,整个操场空空如也,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和远处教学楼里依稀的书声琅琅。
“跑跑吧。”老张说。不等我回答,他就在我前面自顾自地跑起来,速度不快,在等我追上去的样子。可当我追上他的时候,他又总是一句话不说。
老张以“培养体育特长生”为借口,帮我逃过了丢人现眼的罚站,而班主任巴不得眼不见为净。于是,每到该上数学课的时候,我都会跟着老张去操场。他很少开口说话,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们沉默着在操场上绕了一圈又一圈,有时是走,有时是慢跑。
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起,老张开始给我带书,一开始是门口报刊亭里《读者》《青年文摘》之类的杂志,然后是《哈利·波特》,再是《飘》和《百年孤独》。
还有什么比书更适合做孤单少女的朋友呢?我带着一知半解的好奇扎进书的海洋,看到哈利被舅舅、舅妈欺负时会跟着哭,看到斯内普是如何深爱着莉莉,也看到布恩迪亚家族是如何在时代洪流中沉沉浮浮、辗转挪腾的。
我不知道那些书我看懂了多少,可它们像一架通往光明的天梯,一点点引领我走出眼下的泥沼。我又开始向往未来,幻想自己是《基度山伯爵》里的唐泰斯,咬牙想着如何报复班主任和那些诋毁我的人。
我的基本功不差,在摆脱了情绪的困扰之后,成绩迎头赶上并不难。连着两次月考,我都考了第一名,联考的时候更是甩了第二名30多分。
校领导安排我在升旗仪式上讲话,我走下来的时候迎上班主任尴尬又虚伪的笑容,她说:“我一开始就说你有出息,毕竟是黄冈来的,还是不一样。”
那是我曾经无比渴望的肯定与赞扬,可现在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在学校不跟任何人说话,却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与难过。
秋微有句话说得多好啊:“孤僻和孤独是不一样的,孤独是没人能理解你,孤僻却是因为有更厉害的人能理解自己。有些人生活在孤僻里,却一点也不孤独。”
再后来,我成了我们学校那年唯一考上省重点高中的学生。我拿着通知书去找老张报喜,但他不在。我这才意识到我没有他的任何联系方式,电话号码、地址、QQ号,什么都没有。
我上的高中离原来的学校很远,又是寄宿制,平时根本没机会出来,周末又肯定会错过。我等了整整半学期才等到一个出学校的机会,我匆匆跑回来找老张,却发现器材室已经换了人。
新来的老师告诉我,老张离开这里去上海陪女儿了,本来前一年就说要走的,都已经给学校递交了申请,却不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我再也没见过老张,再也没有。无论我怎样在同学聚会上抓着每个人打听,无论我在当年大火的校内网上发起了多少次寻人启事,他就像一滴水珠融進大海,万人如海一身藏。
因而我也从没有机会对他郑重地说声“谢谢”,或者跟他确认当年留下是否因为我。我甚至开始一点点地忘记他的长相和神情,记忆中唯一鲜明的,是我们一前一后在操场上默不作声地绕圈,是他面无表情地把一本本书塞给我。
那是我对老张所有的记忆,也是我对中学时代最好的记忆。那个为我推开一扇门的人,已经转身走掉了,而我将会沿着他打开的那条路,永远步履不停地走下去。